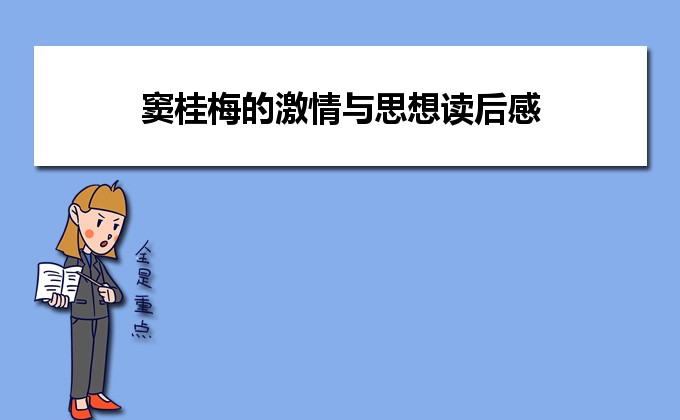ΓΕ÷–΅χ(gu®°)‘ä(sh®©)≈c÷–΅χ(gu®°)°΄ΓΖΉxΚσΗ–
‘ΎΈ“ ÷ν^ΒΡΏ@≤Ω’ψΫ≠ΈΡΥ΅≥ωΑφ…γ≥ωΑφΒΡΓΕεXφRïχ…ΔΈΡΓΖάοΘ§ΓΕ÷–΅χ(gu®°)‘ä(sh®©)≈c÷–΅χ(gu®°)°΄ΓΖ «ΓΕΤΏΨYΦ·ΓΖΒΡΒΎ“ΜΤΣΓΘΏ@ΤΣΈΡ’¬ΒΫΒΉΉς”Ύ ≤Ο¥ïr(sh®Σ)ΚρΘ§Έ“≤Μ÷ΣΒάΓΘΒΪèΡΈ“ ÷άοΏ@≤Ω…ΔΈΡΦ·άοΉςΤΖΒΡ≈≈Ν–μ‰–ρΘ§ΫoΈ“ΒΡΗ–”X(ju®Π) «Θ§Ώ@ΤΣΈΡ’¬ΚΟœώ «εXφRïχΈΡ’¬«ΑΚσΤΎΒΡ“Μ²Ä(g®®)Ζ÷ΫγΓΘΨΆΏ@≤ΩΓΕεXφRïχ…ΔΈΡΓΖάοΒΡΈΡ’¬¹μ(l®Δi)’f(shu®≠)Θ§ΕΦΨΏ”–εXφRïχ¨ëΉςïr(sh®Σ)Κρσw§F(xi®Λn)≥ωΒΡôC(j®©)λ`ΓΔ”ΡΡ§ΒΡΧΊϋc(di®Θn)Θ§”»Τδ…Τ”Ο«…ΟνΒΊ±»”ς¹μ(l®Δi)ΟςΓΔ¥Χ§F(xi®Λn)¨ç(sh®Σ)…ζΜν÷–ΒΡ«ι¦rΓΘ¹Üάο ΩΕύΒ¬’f(shu®≠)ΘΚ…Τ”Ο±»”ς «ΧλΖ÷ΗΏΒΡ±μ§F(xi®Λn)ΓΘεXφRïχ‘ΎΈΡ Ζ’ή“ΜνêΒΡΉxïχΓΔ¨ëΉς…œ¥_¨ç(sh®Σ)”–“ΜΙ…Χλ…ζΒΡôC(j®©)λ`öβΘ§÷Μ «‘Ύ«ΑΟφΒΡ“Μ–©ΈΡ’¬÷–Ώ@ΖNôC(j®©)λ`σw§F(xi®Λn)ΒΡΗϋΕύ“Μϋc(di®Θn)ΓΘάΐ»γΓΕΡßΙμ“Ι‘LεXφRïχœ»…ζΓΖΓΔΓΕ¥ΑΓΖΓΔΓΕ’™Ωλ‰Ζ(l®®)ΓΖ»»ȧΉ¨Έ“ΉxΤπ¹μ(l®Δi)Θ§Η–”X(ju®Π)ΚΆ¨ëΉςΓΕ΅ζ≥«ΓΖΒΡΡ«²Ä(g®®)εXφRïχΚήΫ”ΫϋΓΘΙά”΄(j®§)Ώ@–©ΈΡ’¬ΚΆΓΕ΅ζ≥«ΓΖΒΡ¨ëΉςΡξ¥ζ“≤≤ν≤ΜΕύΘ§ΕΦ «εXφRïχ‘γΤΎΒΡΉςΤΖΓΘΏ@–©‘γΤΎΒΡΉςΤΖΘ§Έ“Η–”X(ju®Π)Θ§Ηϋœώ «Βδ–ΆΒΡ…ΔΈΡΘ§ΤΣΖυΕΦ≤Μ «ΚήιL(zh®Θng)Θ§“ΐΫ¦(j®©ng)™ΰ(j®¥)ΒδΒΡ§F(xi®Λn)œσ≤Μ «ΚήΕύΘ§÷ς“Σ «Ή‘ΦΚ÷ς”^“βΉR(sh®Σ)ΒΡΑl(f®Γ)™]Θ§κSΧéΩ…“äΥϊΒΡΡ«ΖNôC(j®©)λ`”ΡΡ§Θ§ΉxΤπ¹μ(l®Δi)ΚήίpΥ…ΓΘΕχ÷°ΚσΒΡΈΡ’¬Θ§ΈΡ¨W(xu®Π)μçΈΕ‘Ϋ¹μ(l®Δi)‘Ϋ…ΌΘ§¨W(xu®Π)–g(sh®¥)öβΌ|(zh®§)‘Ϋ¹μ(l®Δi)‘Ϋèä(qi®Δng)ΓΘεXφRïχΒΡΈΡΙPΘ§ΥϊΒΡ≈fσw‘ä(sh®©)ïΚ«“≤Μ’™Θ§ΨΆ’f(shu®≠)Υϊ‘Ύ–Γ’f(shu®≠)ΓΔ…ΔΈΡ÷–ΒΡΈΡΙPΘ§ «ΤΪ”Ύ ίΓΔ”≤ΒΡΘ§¦](m®Πi) ≤Ο¥Ζ ‘~κιΨδΘ§ΒΪΨΆΏBΏ@Ο¥“Μϋc(di®Θn)ΈΡ¨W(xu®Π)μçΈΕ“≤‘Ύ÷πùu€p…ΌΓΘ‘ΫΆυΚσΒΡΈΡ’¬ξP(gu®Γn)ΉΔΒΡÜ•(w®®n)ν}‘Ϋ¨W(xu®Π)–g(sh®¥)Μ·Θ§¨ëΉςΖΫ Ϋ÷–ΒΡ“ΐΫ¦(j®©ng)™ΰ(j®¥)ΒδΒΡ§F(xi®Λn)œσ±»±»Ϋ‘ «Θ§’φ”–Βτïχ¥ϋΒΡΈΕΒάΘ§Ζ¬ΖπΥϊΒΡΥΦœκ”…ΈΡ¨W(xu®Π)ΒΡιüΕχ¬ΰόD(zhu®Θn)ΉÉ?y®≠u)ι¨W(xu®Π)–g(sh®¥)ΒΡΨΪΕχ¨ΘΘ§–Έ≥…ΒΡΟΩ“ΜΖN”^ΡνΕΦ≤Μ «ÜΈΦÉë{Ή‘ΦΚΒΡ÷ς”^“β‘ΗΕχ“Σ”–≥δΉψΒΡάμ’™“ά™ΰ(j®¥)Θ§¨ëœ¬ΒΡΟΩ“ΜΙPΕΦ≤Μ‘ΌœώΈΡ¨W(xu®Π)¨ëΉςΡ«‰”κS“β™]ûΔΕχ“Σ“ΐΫ¦(j®©ng)™ΰ(j®¥)ΒδΒΡΙPΙPΫ‘”–Ηυ™ΰ(j®¥)Θ§ΈΡ’¬ΒΡΤΣΖυèΡΩ²σw¹μ(l®Δi)÷vΕΦ‘ω¥σΝΥΘ§ΉxΤπ¹μ(l®Δi)Η–”X(ju®Π)≥ΝΒιΒιΒΡΘ§ΚΟœώ’f(shu®≠)“Μϋc(di®Θn)ΨΆ «¥_ηèΒΡ“Μϋc(di®Θn)ΓΘ÷±ΒΫΓΕΤΏΨYΦ·ΓΖΒΡΒΎ“ΜΤΣΓΕ÷–΅χ(gu®°)‘ä(sh®©)≈c÷–΅χ(gu®°)°΄ΓΖΘ§Μυ±Ψ–Έ≥…ΝΥ‘ΎΓΕΙήεFΨéΓΖ÷–Ω…“‘“äΒΫΒΡ¨ëΉςοL(f®Ξng)ΗώΘ§κm»ΜΓΕΤΏΨYΦ·ΓΖΒΡΈΡ’¬ΕΦ «”ΟΑΉ‘£ΈΡ¨ë≥…Θ§ΒΪ…ώάμ“Μ÷¬ΓΘΥυ“‘Θ§ΥϊΚσ¹μ(l®Δi)ΒΡΈΡ’¬»γΙϊ‘ΌΫ–Ήω…ΔΈΡΘ§Έ“’φΗ–”X(ju®Π)”–ϋc(di®Θn)≤Μ€ (zh®≥n)¥_ΝΥΓΘΈ“Ω²“‘ûιΘ§…ΔΈΡΗϋΕύΒΡ¨Ό”ΎΈΡ¨W(xu®Π)ΖΕ°†Θ§”Ο…ΔΈΡ¹μ(l®Δi)ΖQΚτΓΕΤΏΨYΦ·ΓΖΒΡΈΡ’¬Θ§èΡΈΡ¨W(xu®Π)ς»ΝΠ¹μ(l®Δi)÷vΘ§ΟάΜ·ΝΥΥϋ²ÉΘ§èΡΥΦœκάμ’™¹μ(l®Δi)÷vΘ§Έ·«ϋΝΥΥϋ²ÉΓΘΜρ‘SΈ“¨Π(du®§)…ΔΈΡΏ@²Ä(g®®)Η≈ΡνΒΡΆβ―”‘ΎάμΫβ…œ”–Ψ÷œόΘ§§F(xi®Λn)‘Ύ≤Μ «”–ΚήΕύΥυ÷^ΒΡΈΡΜ·…ΔΈΡΓΔ¨W(xu®Π)–g(sh®¥)…ΔΈΡΟ¥Θ§άΐ»γ”ύ«ο”ξ÷°ίÖΒΡΉςΤΖΘ§Έ“’J(r®®n)ûιΘ§Ρ«÷Μ «²Έ¨W(xu®Π)’Ώ≈ήΒΫ…ΔΈΡ÷–¹μ(l®Δi)―b«ΜΉς³ί(sh®§)ΓΘΈ“¨Π(du®§)εXφRïχΏÄ «ΉπΨ¥ΒΡΘ§≤ΜΡή”ΟΏ@ΖN≤Μ²ê≤ΜνêΒΡΟϊΖQ¹μ(l®Δi)ΖQΚτΥϊΒΡΈΡ’¬Θ§ΙΟ«“ΖQûι’™ΈΡΑ…ΓΘ
½νΫ{œ»…ζ‘ΎûιΓΕΙήεFΨéΓΖΉωΒΡ¥ζ–ρ÷–¨ëΒΫΘ§εXφRïχΖQΥϊ‘γΡξΒΡΉςΤΖ «ΓΑ–Γïr(sh®Σ)ΚρΗ…ΒΡ†I(y®Σng)…ζΓ±Θ§§F(xi®Λn)‘ΎΩ¥¹μ(l®Δi)ïΰ(hu®§) ΙΥϊΓΑώî«“–ΠΓ±Θ§’J(r®®n)ûιΡ« «Υϊ≥…ιL(zh®Θng)Ώ^(gu®Α)≥ΧΒΡ±μ§F(xi®Λn)ΓΘΏ@’f(shu®≠)ΟςεXφRïχ¥_¨ç(sh®Σ)”–“Μ²Ä(g®®)”…ΈΡ¨W(xu®Π)’Ώ≥…ιL(zh®Θng)ûιΈΡ Ζ’ή¨W(xu®Π)’ΏΒΡΏ^(gu®Α)≥ΧΓΘΥϊ‘χ «²Ä(g®®)ΉςΦ“Θ§ΒΪΥϊ≤Δ¦](m®Πi)”–ΆΘΝτ‘ΎΉςΦ“ΒΡ…μΖί…œΘ§ΗϋΏM(j®§n)“Μ≤Ϋ≥…ûιΝΥ¨W(xu®Π)’ΏΓΘ
ΨΆΈ“ΉxΓΕ÷–΅χ(gu®°)‘ä(sh®©)≈c÷–΅χ(gu®°)°΄ΓΖΘ§±Ψ»Υ‰I(y®®)”ύΉxïχ»Υ“Μ²Ä(g®®)Θ§ΨΆ≤ΜΏM(j®§n)–– ≤Ο¥¨W(xu®Π)–g(sh®¥)ΧΫ”ëΝΥΘ§÷Μ’f(shu®≠)ϋc(di®Θn)²Ä(g®®)»ΥœκΖ®ΓΘΏ@ΤΣΈΡ’¬¥_¨ç(sh®Σ)ΖϊΚœΓΑΙήεF÷°ΝxΓ±ΓΘ“ΜΙήΗQ»ΞΓΔ“ΜεF¥Χœ¬Θ§κm–ΓκmΈΔΘ§ΒΪ «¥_ηèΒΡ“Μϋc(di®Θn)“Μ–«ΓΘΓΕ÷–ΓΖΈΡάοΘ§ιL(zh®Θng)ΤΣ¥σ’™ΒΡ“ΐΫ¦(j®©ng)™ΰ(j®¥)ΒδΘ§Ώ@ «ΓΕΤΏΨYΦ·ΓΖάοΈΡ’¬ΒΡΙ≤Ά§ΧΊϋc(di®Θn)Θ§εXφRïχΊSΗΜΒΡ¨W(xu®Π)ΉR(sh®Σ)ΓΔ÷î(j®Ϊn)…ςΒΡ÷Έ¨W(xu®Π)ëB(t®Λi)Ε»”…¥Υσw§F(xi®Λn)Θ§ΒΪ“≤”…¥Υ ήΒΫ“Μ–©»ΥΒΡ‘ç≤ΓΓΘ’f(shu®≠)¨ç(sh®Σ)‘£Θ§Ώ@‰”Βτïχ¥ϋΒΡοL(f®Ξng)Ηώ’φ≤Μ « °»Ϊ °ΟάΘ§ΓΕ‘ä(sh®©)Ω…“‘‘ΙΓΖΈ“ΨΆΡΆ÷χ–‘Ή”Ήxœ¬¹μ(l®Δi)ΒΡΘ§üo(w®≤)’™»γΚΈ≤Μ–άΌpΓΘΒΪ‘ΎΏ@άοΈ“ΏÄ «άμΫβ≤Δ΅@ΌpΒΡΓΘΓΕ÷–ΓΖΈΡΒΡΚΥ–Ρ“β÷ΦΚήΟςΑΉΘ§ΨΆœώΈΡΡ©“ΜΕΈΩ²ΫY(ji®Π)ΒΡΘ§¨Π(du®§)öv Ζ…œΒΡΖΚΖΚΒΡ‘ä(sh®©)°΄≤Δ≈eΒΡ’™’{(di®Λo)ΉωΝΥΨΪ±ΌΒΡ÷Η’ΣΘ§¥_ηèΒΡ÷Η≥ωΨΏ”–ΡœΉΎ°΄οL(f®Ξng)ΒΡ‘ä(sh®©)ΓΔ“≤ΨΆ «…ώμç≈…‘ä(sh®©)οL(f®Ξng)ΒΡ‘ä(sh®©)≤Μ «÷–΅χ(gu®°)‘ä(sh®©)÷–ΒΡΗΏΤΖΓΔ’ΐΉΎΘ§œύ°î(d®Γng)”Ύ…ώμç≈…‘ä(sh®©)οL(f®Ξng)ΒΡ°΄ΓΔ“≤ΨΆ «ΡœΉΎ°΄Ös «÷–΅χ(gu®°)°΄÷–ΒΡΗΏΤΖΓΔ’ΐΉΎΓΘΡ«Ο¥ιL(zh®Θng)ΒΡΤΣΖυΘ§Ρ«Ο¥ΕύΒΡ“ΐΫ¦(j®©ng)™ΰ(j®¥)ΒδΘ§ΨΆûιΝΥΏ@²Ä(g®®)”^ϋc(di®Θn)ΒΡΟς¥_ΓΘΈ“Ω¥ΒΫΏ@άοΘ§°î(d®Γng)ïr(sh®Σ)ΨΆ”–²Ä(g®®)Η–”X(ju®Π)Θ§÷Ν”ΎÜαΘΩ÷–΅χ(gu®°)°΄Έ“≤Μ÷ΣΒάΡ«Ο¥ΕύΘ§“Σ’f(shu®≠)÷–΅χ(gu®°)‘ä(sh®©)Θ§ΆθΨSΒΡ‘ä(sh®©)Οςο@±»άνΑΉΓΔΕ≈ΗΠ≤ν“Μ²Ä(g®®)Φâ(j®Σ)³eΘ§“ρ?y®Λn)ιΓ≠Γ≠‘?sh®©)œ…άνΑΉΓΔ‘ä(sh®©) ΞΕ≈ΗΠ¬οΘ§‘Ό“ρ?y®Λn)ιΓ≠Γ≠Ώ@Ι≈ΆυΫώ¹μ(l®Δi)ΒΡ»Υ≤ΜΕΦ «Ώ@Ο¥’f(shu®≠)Ο¥ΓΘëMάΔΘ§Ώ@’ΐ «”÷“ΜΖNΖΚΖΚ÷°’™ΑΓΓΘεXφRïχœ»…ζ‘Ύ¥ΥΜ®»γ‘SΒΡΨΪΝΠ’™ΉC≥ωΏ@Ο¥“Μϋc(di®Θn)¥_ηèΘ§ΙήΗQεF¥ΧΘ§κm–ΓÖs¨ç(sh®Σ)Θ§Κσ¹μ(l®Δi)»Υ»τΡή™ΰ(j®¥)¥ΥΉς≥ω΅χ(gu®°)¨W(xu®Π)…œΒΡ–¬¨W(xu®Π)Ü•(w®®n)Θ§¥ΥΈΡ°î(d®Γng)”–Μυ ·÷°ΙΠΓΘΓΕ÷–΅χ(gu®°)‘ä(sh®©)≈c÷–΅χ(gu®°)°΄ΓΖΘ§―σ―σ»f(w®Λn)―‘ΓΔèV’ς≤©“ΐΘ§°a(ch®Θn)œ¬“Μ²Ä(g®®)ÜΈΦÉΒΡ≥ΘΉR(sh®Σ)ΓΘΈΡ’¬’φ»γ“ΜâK¥uΓΔ“ΜâK ·Θ§ΧΙΧΙ¨ç(sh®Σ)¨ç(sh®Σ)ΒΡî[‘ΎΡ«άοΓΘ”–“Μ–©»ΥΘ§Μρ’Ώ’φΒΡΨΏ”–ΗΏΒΗΫ^²êΒΡÖs”÷ïΚΈ¥±μ§F(xi®Λn)≥ω¹μ(l®Δi)ΒΡ≤≈¨W(xu®Π)÷ΨœρΘ§Μρ’ΏΨΆ «ΒΆΝ”ΒΡ΅W±ä»Γ¨ôΘ§÷Η’ΣεXφRïχΒΡ¨W(xu®Π)ΉR(sh®Σ)ΈΡ’¬ΓΘΈ“’φœκ¨Π(du®§)Υϊ²É’f(shu®≠)“ΜΨδΘ§Ρζœ»Ήωϋc(di®Θn)Ώ@‰”ΒΡ”≤ΙΠΖρ‘Ό’f(shu®≠)Α…ΓΘ